大秦之道:大道朝天,文章礼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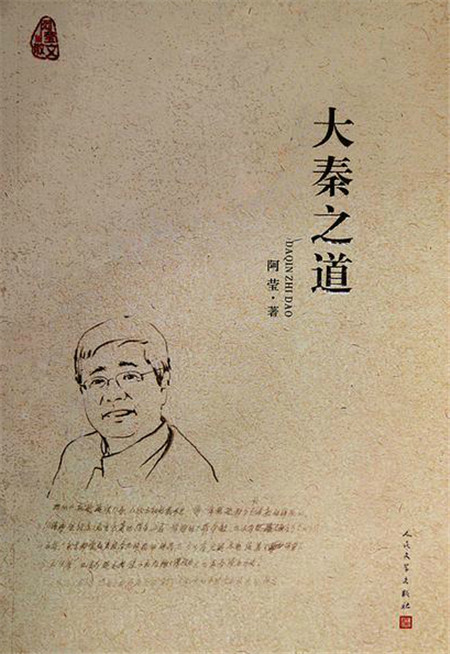
编者按:
作家阿莹先生多年来坚持业余文学创作,先后发表小说、散文百余篇,多篇被收入全国年度选集和中学生课外读物。著有短篇小说集、散文集、报告文学、剧作等十余部。其中,《俄罗斯日记》获冰心散文奖,《米脂婆姨绥德汉》获国家文华大奖特别奖和优秀编剧奖,并获曹禺戏剧文学奖。2013年,我省三十个重大文化项目建设隆重启幕,作者因工作原因有机会一路体察思索并行诸笔底,遂累积成一部厚实的地域历史散文集《大秦之道》,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近日出版发行。书中收录的几十篇美文,悉心搜寻文物遗存背后的故事,体现着作者对三秦文脉的礼敬与挚爱以及对精神家园的坚守与追寻。
本报今天从中择两篇集中刊发,并配发由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先生为该书所做的序言,以飨读者。《天坛之土》经阿莹细腻的笔触和带着浓厚人文关怀的情结,艺术地再现了天坛曾经的辉煌与独特的魅力!
在《横渠之学》一文中,阿莹先生又给我们刻画出一位面对苦厄矢志不渝坚守梦想的关学大儒形象。品读阿莹先生的这些文字,定会给您带来清泉般的心灵滋养与醍醐灌顶般的灵魂涤荡。
我在榆林一座剧场看过《米脂婆姨绥德汉》。
那个剧场是我所喜欢的,是童年时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影院风格,破旧简陋,但是有人气。观众进进出出,不衫不履,嗑瓜子、扇扇子,烟瘾犯了站起来大摇大摆走到大堂抽烟,活生生的百味杂陈的人间。
但大幕启处,是热血男儿,是柔肠百转的女子,是蓝格莹莹的天和莽莽苍苍的地,是悲欢离合,是响遏行云低若游丝的歌。
这样的戏正是人间的戏,戏里人深爱人间,于人于事于物都有情有义。他们走在这俗世里就如远远地走在黄土高坡上,心里是有劲儿的,踏实而敞亮。他们是英雄儿女是俗世男女,也能随时从戏里走出来,走进台下人群。
这是难得的境界。
这戏的作者是阿莹先生。后来我认识了他。
阿莹先生属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投身文学的那一代人。那一代人中,很多人随着时势之变放弃了文学的志向。他们没有错,对文学来说,读的人无论如何应该比写的人多。写作和创造,这注定是少数人的事。而阿莹先生属于坚持下来的少数。“坚持”一词其实也不确切,他不是坚持——顺便说一句,我也不喜欢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常用的词:“坚守”,“坚守”就有一种自我悲剧感。但爱文学的人何须坚持或坚守,比如阿莹先生,以文学的方式与自我相处、与世界相对,这于他不是一件苦事,不过是“悠然见南山”、“相看两不厌”罢了。
在这三十多年里,阿莹先生一直在写,小说、报告文学、戏剧和散文,特别是戏剧和散文,卓然有成。
同时这三十多年里,他也由一个工人一路走来,经历很多事、做了很多事,成为一个高级干部。
谈论阿莹先生的创作,其实都免不了要在做文和做事之间下笔,但这其中的关系似乎又很难说清,大抵也就是止于“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挤出时间写作”云云。
现在,我试着说一说。
三十多年来,阿莹先生的写作从未中断,但从另一方面看,他对中国文学在这三十多年间的种种潮流、风尚似乎不甚在意。即以他后来专注的散文为例,他写乡土,写亲情,写历史文化,写艺术和人生,放在同类题材的书写谱系中,都有一种大道朝天,我自独行之感。他的写作没有“为赋新词”的纠结,没有寻常文人或知识分子的强装和弄险,而是脚下一条路,坦然走过去。读他的文章,你不会惊艳和称奇,你会触动、感动,感到沉静、沉着。
“做文”,包含着一层人工胜天然的意思,要做,常常就不免强做,语不惊人死不休。这当然很好,但事情还有另一面,就是,惊人之语常常不免强行扭曲事物。这在诗歌中或许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在散文中,就有可能变成辞胜于意,变成了对世界与人生的不负责、不诚恳。
所以,我有时很怕除了写散文什么也不干的散文家,因为他只对他的文章负责,对他们来说,做文最重要,而潮流和风尚就是判卷子的老师,不得不时时窥伺风色、揣摩众意,文章就难免浮浪。但如果,散文家在写文章的同时还做着事,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不管是摆个小摊还是负一方重任,他们都会知道,事自有事理,不可轻亵,写文章当然要把话说漂亮,所谓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但把话说漂亮并非为文的目的,为文是为了体人情、明事理。他们的文字是对自己负责、对世界负责的,也许不那么眩目妖娆,但于人心、于世界都更贴切、更亲近。
“修辞立其诚”,这个“诚”字是真诚,也是诚恳。诗歌的写作与世界的关系可能首先是艺术的,而散文的写作与世界的关系肯定首先是伦理的,是一个人恳切地说自己的所知、所感。李白是好诗人,李白却不一定是好的散文家。当然,如果活到现在,李白也尽可在网上发帖子,天马行空,呼风唤雨。
所以,像阿莹先生这样,一边做事,一边为文,对事负责,也对文负责,也就正可以不看潮流,不观风向,只写自己眼前心底的文字。
这部书名为《大秦之道》,起自《石鼓山之谜》,结于《三秦之游》,五十二篇文章,一以贯之,是一个人的路。阿莹先生在陕西这片土地上一路行去,寻幽探胜,抚今仿古。一边走着,有所见、有所感、有所思,行诸笔底,蔚为大观,一个人的路竟被他走成了“大秦之道”,大道朝天,所通者古今之变、文明之理。
新时期以来,写历史、写文化已成为散文巨流,不仅是发思古之幽情,也不仅是重启私家著史、文人论史的传统,更重要的是,对历史、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和看法,在中国依然是一个尖锐迫切的现代性难题,百多年来聚讼纷纭,大概还会争论下去。时至今日,“自我吊打”仍然多见,“翻案文章”“修正史学”也比比皆是;但另一方面,随着国人自信的增强,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如钱穆先生所言,对历史怀着同情的理解,对传统存着温情礼敬之心。《大秦之道》,便是如此。
所谓“同情”,不是以后知之明看当局者迷,而是设身处地,怀着一份体贴的善意,忧古人之所忧,乐古人之所乐,从中领会出先人在他们的条件之下的所以然。由此而生理解,理解先人的艰辛与开创,理解他们的局限与宏阔,由理解而生礼敬之心,在簸荡纷乱的世界上,认同祖国与家园。
这一部书便是温情礼敬之书。
阿莹先生是陕西生人,他写这一切时,心中先存着桑梓之念,这是吾土吾民,是生我养我之地,先人的血在我身上流着,所以,放眼望去,观一切皆有情。
文人论古,常见之病是飞扬跋扈、任性好辩,役古人如奴仆,视万物如刍狗。此病难治,因为病在无情,于古人不亲,并不认他是我的先人。而《大秦之道》为有情之文。于古人先贤有情,于山水有情,于时光有情,于一粥一饭有情,于残碑剩瓦有情……
因为有情,所以有义;因为有义,于这世间担着义务和责任,所以阿莹先生行于大秦之道,便如同老农面对田园生计,目光清明,不任情、不滥情,一切只是珍惜、端正。情中应有理在,他的文是通情达理之文。阿莹先生博雅强记,于乡邦文献多所留意,又曾管过文物、旅游,纵三千年、横八百里,披襟当风,指点今古,这书里有的不仅是知识,更有见识,知识容易见识难,因为这见识断不能靠抄书得来。
情与理,这是散文的根本命题。所谓通情达理,做到很难。古人认为,情动于中,但还要约之以礼。这个“礼”,窃以为就是“理”,就是行于世间的正当和由此而来的表达与书写的得宜。比如阿莹先生的文章,于世间深切用情,但他的看人看物、看山看水、看书看字,其蔼然、肃然,其细腻与脱略、放达与执着,都浸润着诚挚、礼敬。这是性情,也是修炼。情之深浅合度、情之远近得宜,此情与彼情的联类、掩映、平衡等等,自有疾徐轻重的节奏和韵律,这或许就是情达于礼和理和乐的地方。
阿莹先生爱乐,此书中暗自有乐,有大秦之道上的古风。
——终究是写了《米脂婆姨绥德汉》的人。
2016年2月13日改定(作者系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评论家)李敬泽
横渠之学
(阿莹)
这几年眉县的横渠镇忽然热络起来,好多文人墨客都涌过去,想捕捉关学鼻祖的灵感。
我知道那是北宋张载当年在小镇上开过书院的缘故,那书院就称为横渠书院,那张载就称为横渠先生,那学问也就随着纵横的渠水流向关中沃野了。至今那小镇还保持着北宋时的讲坛,且距离很远就有招牌指引,当那白杨树与槐树浓密起来,就会看到一座关中风情的小镇清晰到面前了。这当然是一个古镇,尽管街道两边在竭力仿效城里的风尚,连那店铺的招牌也想表达宏大的念想,但时不时有灰瓦格窗的房屋突兀出来,使人感觉到岁月的叠压和快捷。是的,那张载初出茅庐的时候,应该是位志向远大的青年才俊,曾在北宋嘉祐年间与苏轼、苏辙为同榜进士,却遗憾没有与大文豪结为文学同盟,当然也就没能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后来他转向了《易经》的研究,而且学有所得,居然在丞相的支持下,开坛设学,讲解心款,以致招来年青的程颢兄弟的挑战,双方小试锋芒,竟然自知之明撤席罢讲了。但这场意外的尴尬使他痛下决心发奋研修,从此著述累累,弟子云集,令日后文人学者叹服不已。
在街上行走不远,便有处古风屋檐落入眼帘,院里老树新枝争先恐后伸出臂膀,招徕着被尘世烦扰的匆匆过客,更有黑漆大门挂着的四块牌匾,提醒着人们这里是个探讨学问的地方。当然,这地方的学问应是由张载发端的,他曾经身穿布衣长袍,手握黄色书卷,默默地站在门下发誓创立新说百世流芳,也给沉闷的哲学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思想。这里我无意就他的理论成就繁琐叙述,但必须承认是张载依托这片黄土地,辛勤耕耘,劳苦收获,最终开创了影响中国哲学发展的“关学”一派。
轻轻迈进横渠书院,绿荫遮日,古木参天,廊庑一院又套一院,促人遥想当年先生讲学时的繁华。那时候人们从大江南北汇集这里,多达数百人,绝对是想领悟真知灼见的。当时这横渠镇与京城开封有六百多里,与日渐衰败的长安也有百里之遥,一旦赶到这里坐下听课,便是要能耐得住寂寞的。我细细阅读那一面面介绍先生生平的展板,尽是横渠人想表达的不了情怀,尤其是那篇闻名于世的《西铭》了,更让人感到关中人的一腔热血奔涌而出,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铿锵字句,如钉入案,叮当有声,任谁诵读也会激宕得难以平复了。
可是面前这些粗糙的画板已经褪色,并没能反映张载一生的卓越,反倒是对他的官运愤愤不平。那张载一生二次外放二次进京,似乎很让人扼腕长叹。其实我仔细琢磨,张载首次外放为官是初涉官场的日子,官吏们大都要从低层一阶一阶上来的,何况张载后来还能奉诏晋职为副丞相。尽管只是个副职,却能在朝堂行走,腹中韬略也可直达天庭,绝对是个让官员垂涎的职位,万不能人人都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才算成功吧?而且张载的才干,也曾为丞相王安石所欣赏,曾经力邀他参与革新除弊的事务,但先生显然对丞相的发展思路怀有抵触,竟然婉言谢绝了。既然张载与丞相“不相为谋”,仕途受挫便是必然,各种烦恼也就纷至沓来了。
就像书院里的这些杨树,永远昂着不屈的头冠,也把清高抛到清冷的角落。那年他被外放到浙江宁波,负责审理一桩经济案件,秉公执法,剥笋见心,为当事人洗刷了污名,在当地传为美谈,也算是“为民立命”的实践吧。当然,他最终被贬为周至县管理青竹的小吏,实在是有负先生腹中的韬略了。所以,当王安石变法失败,张载又被神宗召进京城,本已是孱弱之躯了,但他还是妄想施展“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便颤颤巍巍赴京就任了。遗憾啊,开封任上仅仅工作了三个月,便累得旧疾复发,在返回横渠途中竟然溘然长辞了。
所以,这书院里琳琅满目的石碑,有的竖在院中,有的镶嵌墙里,尽是历代骚客来这里留下的笔墨,有的神韵潇洒,有的横竖工整,都在赞扬着一位饱学之士的才华。而这些文人墨客似乎都忽略了张载一心推行“井田制”的执着,这也可能就是他在朝堂屡受轻蔑的根源所在。那“井田制”本是西周时期的土地制度,中为公田,收成上缴贵族,外为私田,收成归为农户,这种制度当时也许有些意义,但最终导致了公田收入的不确定。可是,这种被废除了一千多年的土地制度,却被张载奉为至宝,执意要在全国推行开来,甚至连朝廷的否定都没能使他信念松弛,反而促使先生下决心给朝野做个样子。于是他在眉县买了一块土地,在长安县也购进一块田园,踌躇满志地开始了一场“复古”的试验。
眼前这尊张载的雕像,多少反映了先生的性格,面容清癯,棱角僵硬,一身布衣,两袖清风。我盯着雕像的眼睛心想,这多少有点幽默,那孔夫子一生为“克己复礼”坎坷奔波,到处鼓吹西周的礼秩。而先生却要在自家领地实践西周的土地制度,其行为之固执如出一辙。但今日横渠人显然想回避张载“试验”的结果,居然一字未提。我想这个“试验”当时可能会有点影响的,否则宋神宗怎么会一招再招先生进京议政,这似乎佐证了关学一派为学为人的坚韧,也为后代弟子树立了一个况味难品的榜样。
待走出书院,门匾远了,屋檐也远了,但张载给人带来的震荡还在继续,许多人议起这件让横渠先生念念不忘的“壮举”,依旧是一片啧啧唏嘘。就好比今天有人拥有一块地皮,或要复辟古代均田制,真真执拗得令人啼笑了。我于是思忖,古时文人崇信“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张载却是进退都想兼济天下,都想实践他的一个不醒的梦想,而且他的这种执着,还一代代地影响了关中人的品格。君不见,那后来的关学弟子许多人都以执拗而闻名,有人上书禁烟,敢以死相谏;有人拒接皇诏,敢至死不从;有人国难当头,敢兵谏总统……凡此种种,似乎都能从关学宏论里找到源流,似乎关学之子都有一个梦啊。
我禁不住苦涩地笑了。犟哉,长安城外,关学一派!
天坛之土
(阿莹 )
我没想到在古城密集的楼宇间,会隐藏着一座这般规模的天坛遗存。
那是在陕师大西门南侧,有条被杂乱的商铺拥堵的小道,卖水果、卖小吃、卖杂货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几乎要把房檐掀起来,谁进去转悠都想快点挪出来的。然而,这条喧闹的小道居然有一个文雅的名号:“天坛路”。果然再走进二三百米,朝南一拐又一拐,便见到一个被铁栅栏围住的高大土丘,正被一扇锁着的大铁门护卫着,门口还卧有一方黑色石碑,上刻“唐代圜丘”四个大字,想不到这块土疙瘩竟然在一九五六年就被定为“国宝”了。
然而,听过考古人的讲述,我的眼睛不由地睁大了。这座土丘竟然是一千多年前的祭祀圣迹,古老的天坛似比京城的天坛要高大许多,这不禁让人肃然起敬了。谁都知道华夏民族自古就有“敬天法祖”的信仰,在先民眼中天就是最高的神了,而祭天就是天与人的对话,因而祭天的坛迹便格外的神圣。好奇心驱使我当即推门进去,只见土丘呈现出圆圆的台阶状,南边有条木板搭建的步道直通坛顶。如今已难考证是哪一年始建的天坛,只知道那年隋文帝把皇室搬进后来被称为长安的大兴城,第二年春天便完成了祭天大典。
呵呵,这般神圣啊。站上坛顶就看得清楚了,从下而上有四级高台,每台之间又有十二个陛阶,也就是说上坛需走四十八层台阶,可能寓意陛陛而上与天相会。而陛阶之下则有皇帝静候坛下,想那“陛下”之称也许就是由此衍化而来的吧。而且那坛顶圆圆的平平的,方便天神从任何角度降临这里向人间昭告“君权神授”。
然而站在坛上环顾,陡然发现这尊一千四百多年前的祭祀圣地,已经被四周各色方块建筑团团围住了,尤其那一栋栋高耸的大厦争相挺拔,使得这方昔日圣地难以巍峨起来。不过,面对那些平庸建筑的围堵,丝毫没有影响“挖掘”历史的考古人,他们略感欣慰地说,这方天坛曾经被一层厚厚的黄土覆盖着,是近年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才发掘出来,如今的模样就是隋唐天坛的本真形象。
那坛体上居然可见星星白斑,即使混在黄土里也极易发现。原来古时天坛通体抹有一层白灰,可以想象一座洁白的坛丘,坐落在长安城朱雀门外,沐浴着灿灿的阳光,与红廊灰瓦的朱雀大道相倚相望,多么圣洁,多么纯粹,绝对称得上天下第一坛矣。古时祭天都选择在“冬至”这天,是为“三阳开泰”的良辰吉日。而且祭天的仪规隆重异常,所有皇亲贵胄都要在祭祀前沐浴斋戒,待完成了一系列洁身静心的准备,拂晓前皇帝会亲率百官从城北赶到城南坛下,开始了浩繁的祭祀程序。城里百姓们会拉开门缝遥望绵绵不绝的锦绣队伍,有那胆大的也会溜到天坛附近享受一番眼福,而洁白的天坛则开始静静迎候天子和天神的致敬。是的,隋唐三百多年间,小小圜丘不知目睹了多少次祭祀队伍的顶礼膜拜,那隋朝的文帝、炀帝是一定登临过此坛的,那唐朝的太宗、玄宗也一定在这里祈求过五谷丰登。
遥想那时,队伍浩荡,旌旗招展,鼓乐齐鸣,銮舆缓进,离天坛还有很长距离,皇帝就下了御驾,手持玉璧,恭恭敬敬地向天坛迈步。当身临坛下,听礼部号令,皇亲百官伏地跪拜。皇帝稍稍静默独步登顶,只见坛上神案皇天牌位居中,日月星辰和风雷雨电的神位在侧,后边则放着玉帛牛羊之贡品。然后,皇帝开始咏诵祭文,气息虔诚,声震长安,终于到了天神向皇帝面授机宜的时刻,神圣得连城里百姓也闻声伏地,细细品咂圣人的交流。随后所有祭品被丢进坛下燎炉焚烧,十里之外都会闻到香味,一时间烟雾缥缈,灯影飘摇,一切都变得愈发神秘起来。于是钟鼓瑟齐鸣,四方欢腾,整个长安城便一下子沉浸在祥和之中了,既使祭天队伍离开了天坛,也还会有鼓韵雅乐不绝于耳,使百姓们强烈感受到上天之威严和皇恩之浩荡。
呜呼,古人对天地的敬畏由此可见矣。
然而,我站在裸露的圜丘前忽然遐想,千年的风雨可以滴水穿石,怎么没把这方土丘冲刷成一块泥丸,也许长安天坛真有“上天”赐予的秘籍呢。但那考古人却郑重解释,这天坛能够完整保存,全是因那上面覆盖了一层黄土。我倏然明白过来,这座浑圆的泥质土丘,台阶层层,棱角分明,至今还在释放着一种久违的尊严,的确是内藏玄妙的。这座天坛是在改朝之后被遗弃的,长安百姓一定心存敬畏,担心坛体被风雨剥蚀,便不约而同地集聚起来商议,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给坛体覆上一层厚土。然而,这么高大的坛体如果人背肩挑向上倾土,几乎是愚公移山了,可是再没有万全之策可供选择。于是人们从家里携来铁锨扁担和竹筐,将远处崖畔的黄土一筐一筐挑过来,又一筐一筐背上坛顶倒下去。
一天,两天,三天……
一层,两层,三层……
尽管这个凝聚着长安人悲怆的壮举,文人墨客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尽管不知当时的天空是否阴晴,但人们的心里一定阴云密布,拥堵得呼吸声也断断续续,就连周边围观的老人都扯紧顽童不敢大气出声,就连灶台边的女人也在侧耳倾听咚咚的踏步声。当时的气氛沉闷得快要凝固了,没有舒畅,也没有空灵,因为人们掩埋的不仅仅是一尊天坛,也掩埋了一个王朝的辉煌,掩埋了作为京城子民的荣耀,当然更掩藏了重振天坛雄风的浓重期望!
有人挑担,仰天长啸,一步三叹!
从此长安的繁华与豪迈便被厚厚的黄土掩盖了,从此岁月好像真的从那时起被遗忘了,曾经的辉煌变成了人们饭后茶余津津乐道的残缺记忆,只有那些多愁善感的文人墨客偶尔会聚在城里哪个角落凭吊古韵,聊发一点诗意的狂想。终于,经过千年的风雨洗礼,长安天坛悄然露出了昔日容颜,开始述说新世纪的欢欣了,这给古城的人们带来了持久的亢奋。
是的,多少年来考古人喜欢追随着皇亲贵胄的遗迹,而天坛的重现是得益于人民的创造。正是长安百姓那个天才的壮举,方使得一朝圣迹能够历经千年而风采依旧,正好见证一个民族复兴的不朽梦想。
三秦游QQ群:
三秦游群①:3532197 (三秦文化综合群)
三秦游群②:24288209
(旅游活动群)
三秦游群③:81817349 (车友、自驾活动群)
三秦游群④:70760386 (年票专属群)
三秦游群⑤:146721821 (旅游咨询群)
三秦游群⑥:82616561 (旅行社合作群)
三秦游群⑦:93966174
(陕西特产供应商合作群)
三秦游群⑧:146722047 (投稿群)
三秦游群⑨:134982308 (摄影作品分享群)
互动平台:
新浪微博:http://e.weibo.com/sanqinyou
腾讯微博:http://t.qq.com/sanqinyou
关注“三秦游”微信公众号: sanqinyou 用微信,添加朋友,或扫一扫,以下二维码
编辑:秦人


